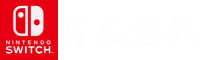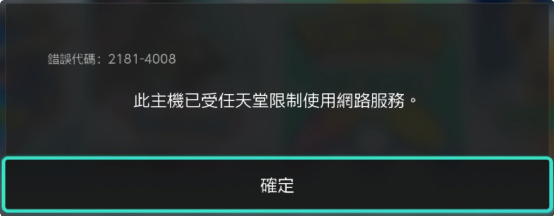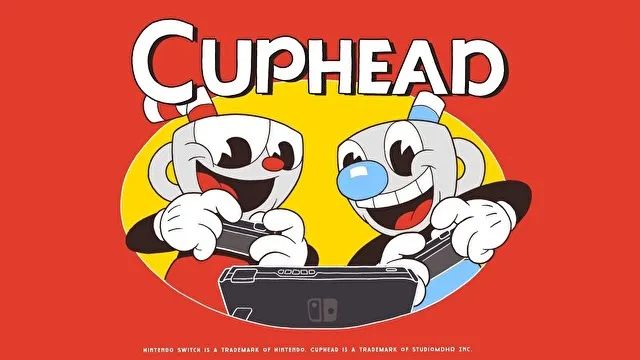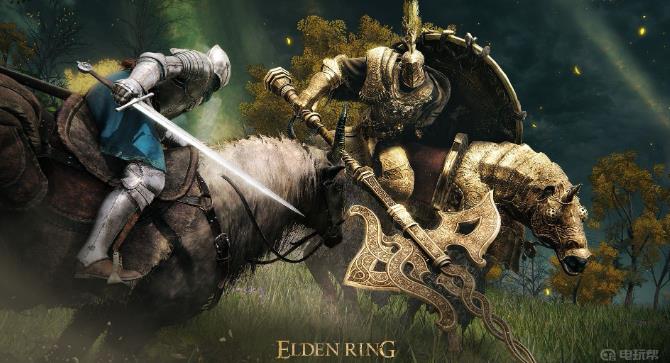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,就有提到這樣一個問題:電子遊戲的遊玩過程再被記錄後,似乎同樣可以達到向觀眾傳遞完整體驗的目的。為了證明這一點,我現在可以很驕傲地(?)向各位宣佈,我從來沒有玩過《最後生還者2》,只是看了主播的錄影,但我寫出了很多評論認為很客觀的遊戲評測文章。你可以點進我的主頁,找到那篇3年前的文字。
啊呀,bigfun倒閉了,你看不見了。不過我把原文章搬過來了,寫得和真的玩過一樣捏。
我的經歷和很多同齡人類似,從小是看著優酷系的遊戲實況主播長大的。那時我甚至把主播遊玩《蝙蝠俠 阿卡姆之城》的視訊下載下來反覆觀看,直到十多年後的今天,我依舊記得故事的每一個細節。
這種經歷很容易讓我產生上述的問題,這也對於業界來說是一個似乎無解的問題。很多作品都會禁止主播直播後續的內容,因為故事是遊戲本身的最大賣點;而有些遊戲則天生適合直播,因為玩家在規則下的遊玩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故事。
讓我們不妨把這個問題的範圍縮小一些,僅僅討論最沒有遊戲性的遊戲——視覺小說身上。在本文中,視覺小說包含了所有的僅有選項或無選項、或遊戲內建玩法非主要遊玩內容的“文字冒險遊戲”,分別對應的例子是《逆轉裁判》《魔法使之夜》和《彈丸論破》。
有關這些遊戲是否是“遊戲”的問題,在學院派的劃分法裡已經歸於“非遊戲”,而且這個範圍要遠大於你我的見解。如果軟體沒有提供影響體驗的主動選擇,那麼這就不是一款遊戲。這意味著,一些步行模擬器,例如《艾迪芬奇的記憶》也被認為和《魔法使之夜》一樣,不是電子遊戲。
這些反直覺的答案很顯然與大眾認知不符。考慮到本文並不打算提出一種全新的標準,延續年數達到全人類的認知產生改變,那麼我還是將“視覺小說”看作遊戲——即便沒有選項,唯一的互動是點選文字,呈現結果和視訊沒有任何區別。
這是為什麼呢?在我看來,電子遊戲的真正唯一特點,實際上是體驗的“時空連續性”。事實上,我可以說電子遊戲不是一種互動的藝術,而是一種新媒體的傳播手段。
“時空連續性”是什麼?在說明這點前,我先要討論一個問題,那就是電子遊戲的敘事的特殊性。
從視覺小說這一最原始,最不先進的遊戲開始,彷彿皮影戲和話劇一樣的演出代表著玩家並非是故事的參與者,而是故事的閱讀者。玩家的遊戲體驗和故事本身沒有多大關係,和軟體系統有關。玩家能夠真正討論的“遊戲體驗”,實際上應該被視作是“閱讀體驗”,是讀完了一本書後也會產生的一樣的感想的型別。其中產生的體驗上的差別,就和無數的哈姆雷特一樣,來自於玩家自身的經歷和閱讀方式。這意味著在“玩家遊玩遊戲”這一場景裡,玩家沒有創造基於遊戲的故事,而是遊戲單方面輸出了故事。
事實上,這種“遊戲單方面輸出了故事”的遊戲,遠遠不止視覺小說這一類,而是幾乎所有線性乃至很多所謂開放世界遊戲,都可以被收容到這個品類裡。嚴格意義上來說,只有少數的遊戲型別可以被收納到逆命題裡,那就是“玩家用遊戲創造了故事”——那就是多人遊戲和機制先行的遊戲。
這意味著我們把遊戲的故事拆成了兩部分:一部分是遊戲提供的故事,另一部分是玩家創造的故事。後者實際上非常模糊,因為但凡我們討論的是軟體,那麼玩家不可能不和電子遊戲產生任何互動。假設我們設計了一個玩家開啟後強制播放且無法跳過的《Never gonna give you up》,播完自動關機的“troll game”,玩家還是與這個遊戲進行了“開啟”的互動。是否開啟遊戲就變成了遊戲性的一環,從中還可以擴充套件到“玩家在視訊播放過程中嘗試強制關閉,但沒有用”“玩家想要截圖,結果失敗”“玩家在直播的電腦被強制關機,直播間一片譁然”等等這些並非遊戲,但與玩家和遊戲本身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的事件。很難去分清楚到底什麼才是“玩家用遊戲創造的故事”,以及這些是否是遊戲本身帶來的體驗。
從前文和本文的一些觀點來看,遊戲的價值實際上就存在於“玩家用遊戲創造的故事”的部分,而不是可以通過其他媒介轉述的前半部分。不過,這其中的差別很微妙,而且由於權重的問題,實際上並非是一個很嚴密的理論。
不過,這已經足夠用來說明有關“時空連續性”了。因為這個理論的重點在於,“雲玩家”所體驗到的,是遊戲能夠提供的兩層故事的集合——遊戲本身的故事和玩家創造的故事。這意味著,假設我觀看了一位主播的實況,那麼意味著我實際上是在消費的不是遊戲本身,而是主播創造出來的“它在遊玩遊戲”的故事。我們的大腦足夠聰明,從主播的行為中分辨出遊戲原本的內容,也能從主播的反應和操作中品味出遊戲本身的遊玩體驗——是一種二手的故事。
對於這種二手故事的消費,其核心已經不在遊玩的遊戲上了,而是主播本身的故事創作能力上。看攻略視訊的雲玩家享受的是“我是大佬”的感覺;看整蠱視訊的雲玩家享受的是主播“低人一等”的節目效果圖一樂;看速通的玩家享受的是一個潛在的勵志故事。
事實上,對於雲玩家的批判倒不如說能被轉化為一個更加普遍的事情的態度:道聽途說的故事、典故、事例,能夠被我們當做有效的經驗嗎?我們能夠確認某些事情的因果關係嗎?這就留給下一篇文章了。現在先說明雲玩家與真正的玩家的本質區別。
從剛才的拆分來看,雲玩家並沒有做出任何和遊戲有關的互動,即使他們可以想象這種互動。不過,所有人都知道,想象和現實是有差距的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,在你的面前有一個不知道多重的箱子,需要搬到100米外的家裡。任何人都有搬東西的經驗,所以即使還沒有搬運這個箱子,但是我們可以想象箱子在不同情況下,自己的感受:“如果是很重的箱子,搬起來會是什麼感覺?自己能不能搬到家裡?”種種。不過,實際搬起來,每個人會因為自己搬箱子的上手方法,體力步速,當前狀態等等,有著大體類似,但細節處完全不一樣的感覺。雲玩家就像是看著別人搬箱子的人——他也可以通過分析等等理解箱子是否沉重,來共感搬箱子是否累人。但是,搬完箱子後體力被消耗,肌肉的痠痛等等,雲玩家只能想象和理解,卻無法真正感受到。“感受的程度會產生差距”——這是雲玩家與真正的玩家是不一樣的根本。
這也意味著這麼一個事實:從某種角度上來看,電子遊戲不像是一種藝術,因為它缺乏了藝術中很關鍵的“對於現實的抽象”(或者說程度上明顯比其他的藝術形式要來的具象)。不同於有可以拖拽的進度條,或是自己放著就可以推行下去的新媒體,電子遊戲本質上就是電子圖畫小說——玩家不閱讀,故事就推行不下去。這種強迫式的特色也就是所謂“時空連續性”的來源——所有的玩家必須被強迫(雖然很多時候都是自願的)進入一段具象的,需要自己推動的“experience”之中。這就帶來了體驗上的根本的差別——看別人做什麼和自己實際做什麼,即使是有著豐富的想象力,也是很難有程度一樣的結果的。
所以,《魔法使之夜》和《霍格沃茨之遺》一樣,都是標準的電子遊戲:玩家不推進,那麼故事就會停止不前。
等等,我們似乎忘記了一個問題:這種電子小說是有“自動播放”按鈕的呀!那麼,用自動播放遊戲全程,是不是也和雲玩家一樣?那麼所謂的玩家的“時空連續性”的強迫,那不就不復存在了嗎?
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:我們主要討論的是形式上的“欣賞藝術”的方法所反映的“藝術”之間的區別,但沒有討論是否是以“完整尊重的態度”為基礎,展開“觀眾”“玩家”對於“藝術”的欣賞的。
展開這個話題,就會回到上面我們擱置的討論裡。於是,本文就先到這裡吧。
下一篇是有關電子遊戲實際潛在價值,當然,還有有關視覺小說真正的獨特魅力和不可取代性的理論。